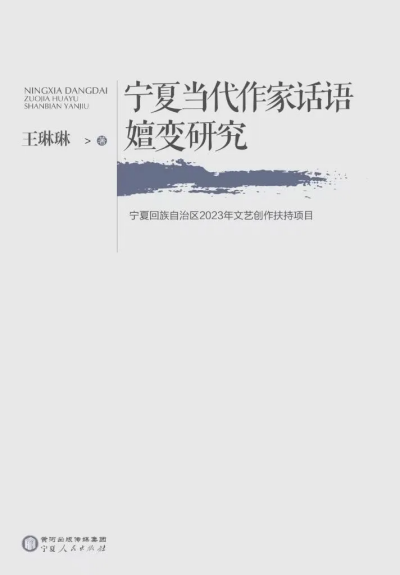这是王琳琳继《张贤亮文学和电影作品比较研究》之后,又一部以宁夏当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,也是当代宁夏文学研究的又一新的学术成果和重要收获。
当代宁夏文学的崛起,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(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,即有路展、哈宽贵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儿童文学、小说作家,但并不能反映宁夏文学的整体水平),以“两张(张贤亮、张武)一戈(戈悟觉)”的复出、出现为标志,尤其是以张贤亮复出后的小说创作为标志。1980年,读了张贤亮的作品后,评论家阎纲惊呼“宁夏出了个张贤亮!”自此,张贤亮被视为当代宁夏文学最具实力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,成了宁夏文学的一棵大树。事实也正是如此,20世纪80年代,张贤亮作为最能代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小说发展杰出成就(夏志清语)、最具批评精神(冯骥才语)、最有思想家气质(赵俊贤语)的作家,几乎是以一己之力,撑起了宁夏文学的一片天空,使得宁夏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,而且是重要的一席之地。张贤亮的成功,产生了井喷效应,在张贤亮这棵大树的影响、呵护、扶持之下,宁夏文学有了自己的“三棵树”“新三棵树"……最终形成了郁郁葱葱的一片林。宁夏成了“文学最宝贵的粮仓”,文学成了宁夏“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的最好庄稼”(铁凝),也因此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中的“宁夏现象”(刘大先语)。就此而言,研究张贤亮,研究文学的“宁夏现象”,对当代宁夏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来说,都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。这也正是王琳琳两部学术著作的意义、价值所在!
如果说,王琳琳的前一部著作研究的是张贤亮这棵树(而且是棵大树!)的话,那么,这部新著则是以宁夏文学这片林(而且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!)为研究对象的。两相比较,不仅仅是研究范围的拓展、研究视野的扩大,更主要也更重要的,是研究方法的探索和理论意识的强化。
全书五章,分为两部分:
前两章侧重于理论构建,后三章侧重于文本细读。两部分之间恰好构成了一种互证关系。理论探索是王琳琳读书时就有的学术志趣,而文本分析则正是其文学研究所长。真正的文学研究,既要追求学术学理,又不能忽视艺术审美。追求学术学理,离不开理论的支持;讲究艺术审美,则离不开文本的细读。王琳琳的这部著作,正是这二者结合的产物,写得既学术,又文学。
《宁夏当代作家话语嬗变研究》
作者:王琳琳
出版社: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
具体而言,本书的特色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第一,宁夏当代文学研究内容、范围的拓展。以往的宁夏当代文学研究,偏重于小说的研究(毋庸讳言,最能反映、代表当代宁夏文学成就的,当属小说创作),而且偏重于小说作家作品的个案解读,对其他文体(如散文、影视剧、非虚构写作等)、文学现象(如作家的代际划分、差异及其原因等)关注不够。王琳琳的新著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或不足。书中对当代宁夏文学制度建构(尤其是文学制度现代化)的讨论,对当代宁夏文学“大”“小”传统的梳理,对当代宁夏文学。影视剧交汇融合的分析,对当代宁夏作家代际的划分及其差异的解读,等等,都是以往的宁夏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少见甚至没有的,拓展了当代宁夏文学研究的疆域。
第二,宁夏当代文学研究范式、方法的探索。研究疆域的拓展,需要有相应的理论、方法的支撑。过往的宁夏当代文学研究,与充满探索的勇气、执着,创造的智慧、活力的宁夏文学创作相比,其创新创造的动力、活力明显不足,观念、方法逐渐陷入了某种窠臼、程式、套路,渐趋僵化、刻板,而且同质化的现象日渐突出。王琳琳的新著部分地改变了这一状况。书中以宁夏当代文学话语变、话语特色为中心,综合运用文化学、媒介传播学、叙事学的理论、方法,从媒介记忆、媒介交融和媒介符号多个方面,描述、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宁夏文学的生成、演进,诠释、评价其价值、意义,为当代宁夏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和可能。
第三,宁夏当代文学话语特色、体系的发现。文学研究必须以文本细读为基础、前提,通过文本细读,方有可能有新的发现,从而言人所未言、发人所未发。王琳琳的新著正是如此。书中通过文本细读,梳理、凝练了宁夏当代老生代、中生代、新生代几代作家话语特色,不仅发现了其中的代际差异、个体差异,而且注意到了其间的代际传承与多元共生。在此基础上,进而发现、讨论了宁夏当代文学的话语体系,指出,这一话语体系集中表现为建立在开阔、开放的民族认同、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乡土、伦理和成长等多元话语的相伴相生,为宁夏当代文学研究创设了新的评价标准。
(本文发表于《宁夏文艺家》报2025年第1期14版)
(编辑:贾雨晴)